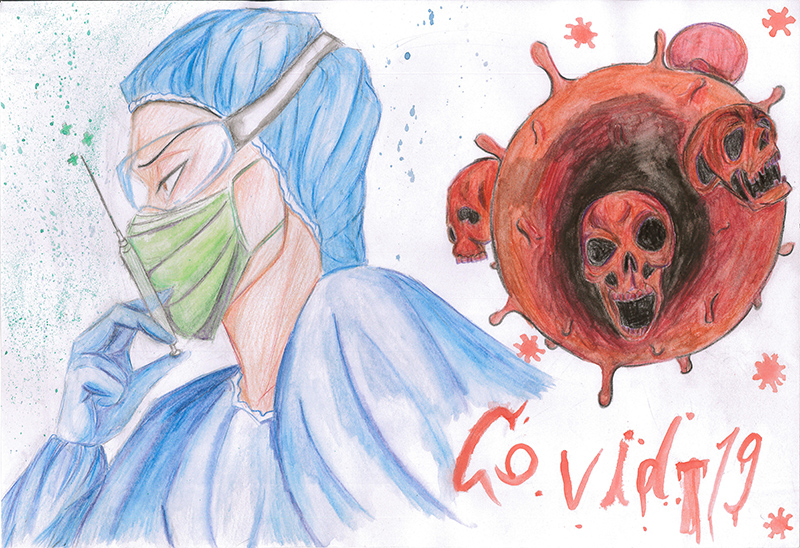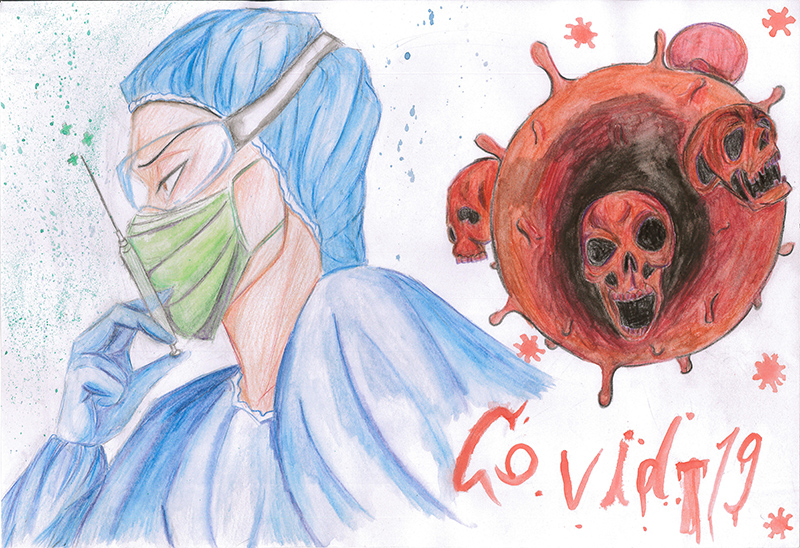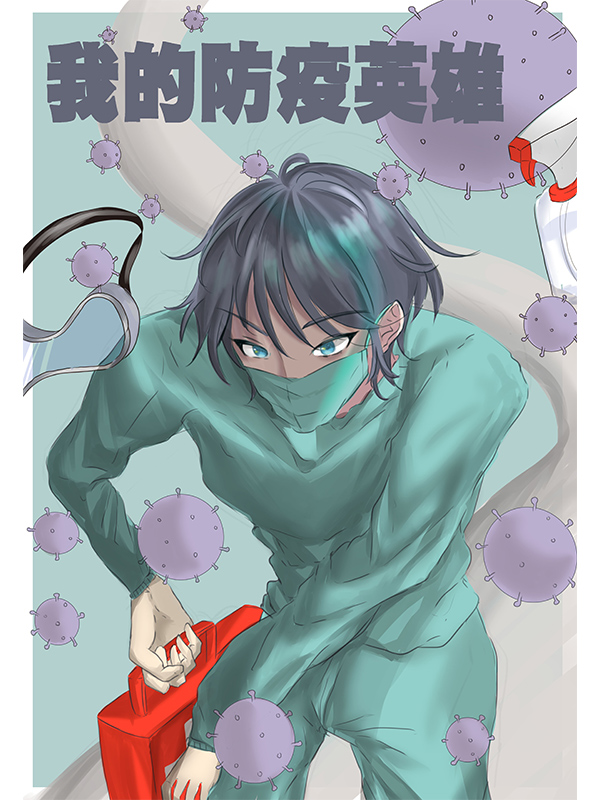引言
距SARS (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疫情約18年(2002)的今天,我們再度面對因冠狀病毒所引發的疾病(COronaVIrus Disease-2019 ; COVID-19)的威脅---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。COVID-19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、全球的經濟結構,以及心理世界的輪廓。
COVID-19於2019年末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首次被發現,隨後在2020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,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。截至2021年10月7日,全球已有累計報告逾2.36億例確診個案,其中超過483萬人死亡,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流行病之一。由於從感染病毒至症狀浮現之間的潛伏期可長達14天,甚至有24天的案例,而且即使沒有發燒、沒有感染跡象或僅有輕微類似流感症狀的感染者也具有傳染力,因此症狀篩檢無法有效檢測,導致疫情不易掌握。同時,雖然COVID-19主要藉由人近距離接觸傳染,但它亦被發現可以通過被污染的物品表面等環境因子傳播。這意味著COVID-19比中東呼吸症候群(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; MERS)或SARS的疫情更難控制。據報導,這次疫情僅花四分之一的時間就造成SARS事件十倍的確診數字。更令人憂心的是COVID-19病毒已經出現至少2次變異,傳染性亦急劇增強。因此,面對尚在持續中的COVID-19疫情,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。儘管新冠肺炎的致死率不是特別高,但只要機率不是零,就難免有面對死亡的疑慮。無論是自己或親友的死亡,對許多人而言,就像是世界將毀滅般的恐懼,或者聯想起對逝去親友的悲傷回憶。儘管在台灣的疫情比起世界其他大多數的國家,已經是非常安全。但隨著疫情警戒等級的升降,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接觸仍需有一定的安全規範。許多活動皆改以通訊方式進行。尤其在疫情嚴峻期間,人與人、家庭與家庭、團體與團體,甚至不同城市之間的往來,都必須加以限制。有必要面對面時也必須戴好口罩。長時間面對束手無策的疫情蔓延,生活很容易會變得缺乏意義感,讓人心生放棄努力的念頭,也可能變得較麻木地生活。新冠疫情讓人與人相處的溫度改變了多少?孤獨的人比較不會被傳染,但面對孤獨的焦慮該如何應付?在疫情阻隔下所出現的困擾與不安又該如何面對?
新冠肺炎讓我們不得不正視生命的限制與意義,認真看待藏在心底且難解的疑惑與焦慮。